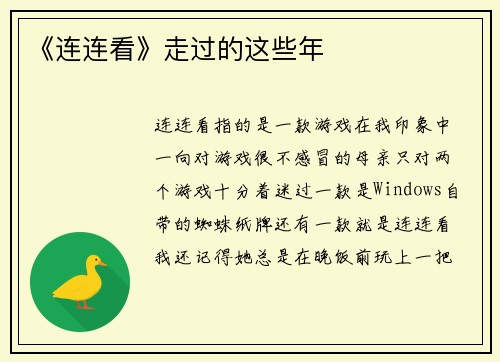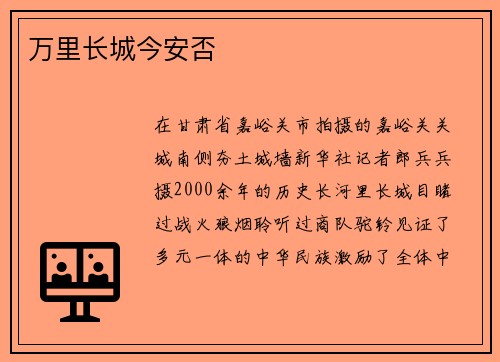【三国名城录】苍梧和南海:三国时期的两广风云(4)
七、陶璜三定交州
好大喜功的孙皓不能容忍晋国把势力伸入交趾,威胁吴国的战略后方。吴建衡元年(269年),孙皓又命监军虞汜、威南将军大都督薛珝、苍梧太守陶璜从荆州,监军李勖、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,先至合浦会合,然后进攻交趾。

虞汜为虞翻之子,薛珝为薛综之子,两人都是出自儒学世家,擅长内政外交,军事则非其所长。所以荆州这一路军,实际的指挥官是陶璜。不过,虞汜为监军,薛珝为大都督,他们虽不精通军事,但仍有很大的话语权,所以这一路军的指挥系统,难免有些混乱。陶璜与杨稷战于分水,果然因诸将各行其是,陶璜大败,手下两名大将阵亡。
这时薛珝打算甩锅,他指责陶璜:
“若自表讨贼,而丧二帅,其责安在?”
意思是这次出战是陶璜自己申请的,战败的责任要由陶璜来承担。
陶璜不是逆来顺受的冤大头,他不甘示弱地辩解道:
“下官不得行意,诸军不相顺,故致败耳。”
意思是他没有完全的指挥权,没法指挥调度诸军,要担责也不该是他来担。
东吴名将:陶璜
被下属当面顶撞,薛珝当然很不高兴,差点就下令撤军了。幸好陶璜突出奇计,以数百兵渡海突袭九真太守董元,掠得一批宝物,用船运回来献给薛珝。薛珝感到倍儿有面子,这才笑逐颜开,不再提撤军之事,并上表推荐陶璜为交州刺史。
吴军的另外一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监军李勖、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前往合浦,大概是遇到风浪,进军不太顺利。李勖也是个善于甩锅的主儿,他杀了负责导航的将领冯斐,决定撤军。
李勖擅自撤军,闯下大祸。殿中列将何定向孙皓上奏:
“少府李勖枉杀冯斐,擅撤军退还。”
这个何定,类似于孙权时期的吕壹,是佞幸出身,专以告密构陷为能事,充当孙皓打击朝臣、维护专制的工具人。本来,李勖撤军系事出有因,论罪应不至死。但何定曾为儿子求娶李勖之女,而李勖看不起何定的出身,拒绝了这门亲事,因此得罪了何定。这时,何定抓住了李勖的把柄,在上奏李勖撤军一事时添油加醋、罗织罪名,拼命把李勖往死里整。
果然,何定的上奏惹得孙皓大怒,下令“诛(李)勖及徐存,并其家属,仍焚勖尸”。可怜徐存,本来没他什么事的,也被连累着一起被杀害了。
出师未捷,先杀主帅,这对交趾征伐军的士气影响很大,陶璜等人一时无力发动攻势,战局陷入胶着。
但陶璜不愧为一代名将,足智多谋。他见军事上讨不到便宜,改而采取策反的办法削弱敌军。
吴凤凰二年(273年),陶璜通过游说、贿赂等手段,策反了扶严贼帅梁奇。扶严是交趾郡的一处地名(今越南太原省太原市一带),为骆越族人聚居之地,所谓“贼帅”,当是指骆越豪族首领(梁氏至今为壮族大姓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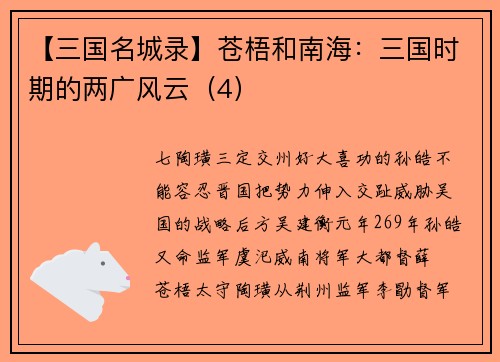
梁奇归降陶璜后,亲率一万人加入吴军,吴军军势大振。更重要的是,梁奇的归降,表明交趾蛮夷已经倒向吴国,不支持晋国势力进入交趾,杨稷等人失去当地蛮夷的支持,在交趾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。
紧接着,陶璜又策反了杨稷部下的将领解象。解象还有个哥哥解系,是杨稷部下级别更高、战力更强的勇将。陶璜为了招徕解系,让解象写密信劝降解系,并和解象一起乘着刺史专用的高大辂车,在军营中巡行,一路鼓吹欢呼,好不威风。杨稷一看这架势,连解象都有这种待遇,解系迟早也会顶不住诱惑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把解系杀了。
事实证明,杨稷杀掉解系,是一大失策。这不仅自毁长城,失去一大战力,而且令军中将士兔死狐悲,无不心寒。
凤凰二年(273年)七月,陶璜了解到交趾城中人心涣散,不失时机地向杨稷劝降。在此之前,由于当地蛮夷纷纷归附,陶璜手下兵力已达十万之众,完成了对交趾城的四面合围。小小交趾城哪里顶得住十万大军四面进攻,而且,交趾城中的军粮已经耗尽,杨稷再怎么能打,也无力翻盘了。
但是,杨稷要想投降,还面临一个法律问题。
当初,南中监军霍弋派杨稷等人前来交趾,约定:
“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,家属诛;若过百日救兵不至,吾受其罪。”
原来,杨稷等人进兵交趾,家属还留在南中,相当于人质,如果杨稷等人在交趾被围困,要坚守百日,没等到救兵来,方可投降,如果没有守满百日以待救兵,就要杀掉家属。
早在一年多之前,陶璜就开始进攻交趾了,但十万大军对交趾城完成合围的时间不长,尚未满百日,因此还不符合杨稷和霍弋约定的投降条件。只是,杨稷军粮已尽,守也守不住了,只能向陶璜乞降。
陶璜很仁义,他知道如果此时接受杨稷的投降,那杨稷他们留在南中的家属必死无疑,所以他拒绝了杨稷的投降,并送军粮进入城中,让他们守满百日后再降。实际上,陶璜早已得到情报,南中监军霍弋在不久前病故,现在南中蛮夷叛乱频发,不可能派援兵到交趾来了。
事情正如陶璜所料,百日之后,南中并无一兵一卒来到,杨稷等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城投降。投降之后,杨稷发病而死,毛炅因曾杀害刘俊、修则,被斩首,当年跟随杨稷前来的孟干、李松、爨能等诸将,都归降了东吴。
晋国这一次以南中监军霍弋为战略支撑,派兵经营交趾的行动,看似无关大局,但实质上是篡位立国不久的司马氏对东吴的一次军事试探。要是试探成功,那么晋对吴将形成北、西、南三面合围的态势,战略优势进一步加强,甚至有可能提前发动灭吴之战。只是由于试探失败,表明东吴尚有相当的实力,不可遽败,以致司马氏不得不放弃在短期内灭吴的打算,改为长远谋划。
八、郭马之乱
陶璜平定交趾之乱,挫败了晋国在东吴后方开辟根据地的战略企图,巩固了孙皓的统治。孙皓其实是个有一定能力的君主,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,来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,他在历史上留下的“残暴不仁”的恶名,不过是他防范和打击权臣、维护皇权专制的一个侧面罢了。
孙皓:随时准备刀人
出兵平定交州,也是孙皓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。平定交州后,孙皓又开始在行政区划上玩花样,主要措施是新设广州,以及从苍梧、郁林、交趾等郡分出若干县,设立新郡。设立新的州郡,可以削弱原有州郡的实力,防范地方势力过大进而威胁皇权,同时,新设的州郡可以安排孙皓信得过的人担任刺史、太守,笼络一批人心。
新设广州,早在吕岱任交州刺史时就提出过了。但在当时,这是为了削弱士氏家族势力的一种策略,在士氏家族被灭以后,这一策略就失去了意义,因而并未付诸实施。
到了孙皓时期,由于交州动乱频发,有必要加强郡县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,为此需要分设更多的郡县。
新设的广州,包括原来交州所辖的南海、苍梧、郁林三郡,同时,从南海郡分出高凉郡(治高凉县,今广东阳春县)、高兴郡(治广化县,今广东阳江市)、始兴郡(治曲江县,今广东韶关市),从苍梧郡分出临贺郡(治临贺县,今广西贺州市八步区),从郁林郡分出桂林郡(治潭中县,今广西柳州市区),并从荆州零陵郡分出始安郡(治始安县,今广西桂林市区),划归广州。
广州分出后,交州就只剩下原有的交趾、合浦、九真、日南四郡,实力大大削弱。这大概是东吴政权鉴于吕兴之乱,采取的压制交州的策略之一吧。同时,从交趾郡分出武平郡(治武定县,今越南太原省太原市一带)、新兴郡(治麋泠县,今越南永富省安朗县一带)。分出武平郡应是为了酬赏归附的梁奇等扶严夷首领,分出新兴郡就很明显是要削弱交趾郡的实力了。
通过新设广州以及武平、桂林等郡,使岭南地区的州郡碎片化、弱小化,一郡生乱,就会遭到周边各郡的讨伐,从而实现势力均衡,保持地区稳定。孙皓自以为得计,岭南地区应该高枕无忧了。
交广两州分立,始于三国吴
可是,孙皓万万没想到,问题恰恰出在新设的州郡里。
凤凰三年(274年),东吴从郁林郡分出潭中、武丰、粟平、羊平、龙刚、夹阳、武城、军腾八县,设立桂林郡,治潭中县。“桂林”之名自古有之,秦始皇平定岭南后,设立桂林郡,治布山县,后改为郁林郡。如今孙皓再设桂林郡,乃是旧瓶装新酒,用了“桂林”这个名儿,地方却不在原来的桂林,当然也不是现在的桂林(现在的桂林那时叫始安郡),而是现在的柳州。
东吴新设桂林郡后,太守是谁,因为史书无载,不得而知。
但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,
天纪三年(279年),“(修)允转桂林太守”。
由此可知,在天纪三年(279年),桂林太守一职出缺,合浦太守修允调任桂林。修允为大都督修则之子,曾随陶璜南征交趾,颇有战功,封为合浦太守,由这样一位与交州有缘的官员出任桂林太守,本是合适人选。可惜此时修允身体不太好,正在番禺就医。接到任命后,他让手下的部曲督郭马先领五百兵至桂林,以稳定状况。但郭马尚未出发,修允就病死了。
修允的突然死去,引起了郭马的恐慌。
郭马慌什么呢?这就要说到具有东吴特色的私兵制度了。
原来,自秦汉以来,有势力的大家族总会有一定数量的家奴,称为“部曲”,他们和家主之间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孙策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,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部曲制度,并且允许部下将领将各自的部曲按照军队的管理方式组织起来,成为专属于将领个人的“私兵”,这些“私兵”可以继承,在将领死后,“私兵”由其嗣子继续统领,因此也称“世袭领兵”制。
这样做的好处,一是有助于增强将领和士兵的感情联系,保持忠诚度和战斗力,二是“私兵”由将领自己想办法供养,不用国家财政负担,可以节省大笔开支。
同时,“私兵”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,那就是不利于君主掌控军队,不利于君主专制。在东吴孙氏创业之初,为了激励将领效力,孙策、孙权对“私兵”制度的弊端还是能够容忍的,但在政权巩固后,“私兵”制度就越发引起孙氏君主的警惕,逐渐削弱甚至废除“私兵”制度。到了孙皓时期,能够拥有“私兵”以及“世袭领兵”只是极少数官职极高、战功显赫的高级将领的特权,一般人不允许“世袭领兵”了。
修允这个太守级别的将领,说起来官职也很高了,但仍不能“世袭领兵”,所以修允死后,他的部曲私兵要被编入其他将领的军队中。郭马和他的同袍自修则时期就在一起共事,历经两代主公,感情很深,他们不想被政府强行解散分离,遂密谋起兵反抗。
修允死时,郭马还在南海,尚未出发前往桂林。正好这时孙皓命人在广州清查户口,闹得人心惶惶,郭马与部曲将何典、王族、吴述、殷兴等商议,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煽动南海军民造反。
孙皓清查户口,为什么导致人心惶惶呢?那是因为,在唐朝实行两税法之前,收的是人头税,一些农民交不起税(或不愿服兵役、徭役),只能逃亡至异乡,称为“逋户”或“逃户”。这些逃亡的“逋户”“逃户”,往往投靠有势力的世家大族,由他们帮助隐瞒户口,从而达到逃税的目的。“逋户”“逃户”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,历来是国家立法和司法打击的重点,但凡是比较强势的政权,都多多少少会采取一些清查户口、防止瞒报漏报的措施,以增加税收,增强实力。
bb贝博官网不过,话又说回来,当时“逋户”“逃户”是普遍的社会现象,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,要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注意方式方法,从原因着手,减轻老百姓的负担,否则,一味的严打重罚,效果只会适得其反。
以孙皓残暴不仁的做派,他在广州清查户口,大概就是不注意方式方法、一味用强的那种,因此既得罪了当地的世家大族,又让交不起税的“逋户”怨声载道。郭马等人正是利用了此时广州士绅和农民对孙皓极度不满的情绪,以手中的五百兵马为基础,同时煽动各处军队和民众共同起兵造反。
郭马之乱,约在天纪三年(279年)八月左右。叛乱来势甚大,郭马等人一举攻杀广州都督虞授,又杀南海太守刘略,驱逐广州刺史徐旗。郭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,封殷兴为广州刺史,吴述为南海太守,命何典攻苍梧,王族攻始兴。
东吴执金吾滕修,刚被孙皓拜为三公之一的司空,尚未举行“拜”(任命)的仪式,又转为镇南将军、假节、领广州牧,率万人征讨郭马。之所以用滕修为将,是因为滕修曾经当过广州刺史,在岭南有一定威望。但可惜的是,滕修虽善于治理蛮夷,但领兵作战却非其所长。滕修以万兵进至始兴,正好碰上王族在攻打始兴,滕修与王族交战,竟不能胜,被阻挡在始兴城外。
孙皓见滕修不能取胜,又遣徐陵督陶濬(陶璜之弟)率七千人南征广州,又命交州牧陶璜率所领交趾、合浦、郁林诸郡兵,两兄弟从东西两面夹击郭马。
陶濬:陶璜之弟,但才能与哥哥相差甚远
徐陵即京口(今江苏镇江市),是拱卫建业的要地。陶濬镇守徐陵,所率当是吴军精锐,故而孙皓并未第一时间出动这支精锐,直到滕修进兵受阻,孙皓才动用这支精锐。
孙皓忙着调兵遣将南征广州的时候,北方的中原大地正在发生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。
天纪三年(晋咸宁五年,279年)十一月,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出兵二十余万大举伐吴,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,镇军将军、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,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,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,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,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,龙骧将军王濬、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兵浮江而下。六路大军水陆并进,浩浩荡荡,大有一举扫平东吴之势。
晋军大举伐吴
晋军大举伐吴,打乱了孙皓南征广州的计划。陶濬所率精兵,行至武昌,听闻晋军来伐,一时手足无措,不知所向,在武昌滞留了一个多月,才决定掉头赶回建业。陶濬这一来一回,就错过了与晋军先锋决战的机会。
原来,在陶濬赶回建业之前。孙皓已派丞相张悌、副军师诸葛靓等率兵三万渡江迎击王浑。张悌的三万大军中,有丹杨太守沈莹指挥的丹杨锐卒“青巾兵”。丹杨兵自古以来就是闻名天下的精兵,汉末大乱时,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都曾派人至丹阳征兵。沈莹的这支“青巾兵”,可以说是东吴最后的王牌部队。但是,两军在版桥一战,结果却是吴军大败,张悌战死。
版桥之战,对吴军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因为这一战的结果表明东吴最精锐的军队也不是晋军的对手,再加上孙皓多年的暴政,丧尽人心,有才有能的文武将官已被屠戮殆尽,所剩多为庸碌之人,虽有吾彦、陶璜之流尚可一战,但却偏居一隅,难以影响全局。版桥之战过后,吴军已经全无战意,士气濒临崩溃,再也没有与晋军决战的能力了。
天纪四年(280年),陶濬才磨磨蹭蹭地回到建业。此时的建业,早已人心惶惶,东吴政权如同风中之烛,崩塌在即。但陶濬刚从外边回来,似乎没有察觉到异常。
在陶濬觐见孙皓,孙皓问起晋军水军情况时,陶濬还大言不惭,称:
“蜀船皆小,今得二万兵,乘大船战,自足击之。”
孙皓一向喜欢吹牛,他听了陶濬吹的大牛,非常高兴,授陶濬节钺,令其集合两万人的军队,反击晋军。
然而,现实是残酷的,已经没有人愿意为孙皓卖命了。那勉强集合起来的两万人,一夜之间就逃跑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陶濬这个光杆司令在风中凌乱。
此时,司马伷、王浑、王濬的大军都已经逼近建业。孙皓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,派人奉书请降。至此,立国八十六年的东吴政权遂告灭亡。
王浑
南征广州的镇南将军、广州牧滕修,在始兴郡得知晋军来伐,立即退兵回援。但是已来不及了。滕修走到巴丘,孙皓就投降了。晋武帝诏以滕修为安南将军,广州牧、持节、都督广州军事如故,事已至此,滕修也不再折腾,乖乖地降了西晋,继续当他的广州牧。
南征广州的大军中还有交州牧陶璜。孙皓投降时,陶璜还在攻打广州。孙皓手书一封,命陶璜之子陶融送至陶璜手上,陶璜览书流涕数日,也无可奈何,只能投降归晋,遣使送印绶诣洛阳。晋武帝下诏复其本职,也就是继续当交州牧,只是改其前将军为冠军将军,加封宛陵侯。
至于叛将郭马,史书却没有记载其结局如何,大概是同样归降西晋了吧。
郭马之乱发生在东吴天纪三年(279年)八月左右,三个月后西晋就大举伐吴,郭马之乱成功地牵制了陶璜、陶濬、滕修等三支部队,使其无法投入长江防线,客观上使得王浑、王濬等突破东吴长江防线变得更加容易。
假如没有郭马之乱,张悌在渡江迎击王浑时能将陶濬、滕修的部队纳入麾下,那么其兵力将达到五万,与王浑大体相当,那样或多或少会对战局产生一些影响,至少东吴不会灭亡那么快。
这样一来,就不禁令人怀疑,郭马之乱究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,还是西晋王朝有意策划的大战略?
晋武帝司马炎
在郭马之乱前,东吴还发生了一件看起来不算什么大事的事件。话说当年霍弋为经营交趾,派杨稷为交趾太守,率毛炅、董元、孟干、孟通、李松、王业、爨能等一批将领前往交趾赴任,陶璜平定交趾时,董元战死,杨稷病死,毛炅被斩,其余孟干、李松、爨能等投降了东吴。孟干被迫降吴,心里很不服气,他辗转逃亡入晋,至洛阳向晋武帝进陈伐吴之计,晋武帝赞赏其计,厚加赏赐,命其为日南太守。
关于伐吴之计,羊祜、杜预、张华等武将谋臣已经和晋武帝反复论证过不知多少次了,蛮夷出身的边鄙将领孟干有什么妙计,能够让晋武帝大加赞赏呢?结合孟干在交州领兵作战的经历以及他对交州情况的了解,他向晋武帝进陈的伐吴之计,很可能就是在岭南交州地区制造动乱,牵制东吴的兵力,使伐吴大军更容易突破长江防线,攻至建业。
所以,晋军伐吴的时机,好巧不巧,正好在滕修、陶濬等人南下的时候,这或许是出自孟干的策划,亦未可知呢。
三国时期的两广风云,在诡异的郭马之乱中画下了句号。进入西晋时期,岭南地区的治理基本沿袭东吴模式,甚至连两州州牧的人选都没换,广州牧仍是滕修,交州牧仍是陶璜,交广两州分离的行政区划因此日益巩固下来。郡县的设置也更加细致,一些沿袭至今的地名开始成型,影响可谓深远。
(全文完)